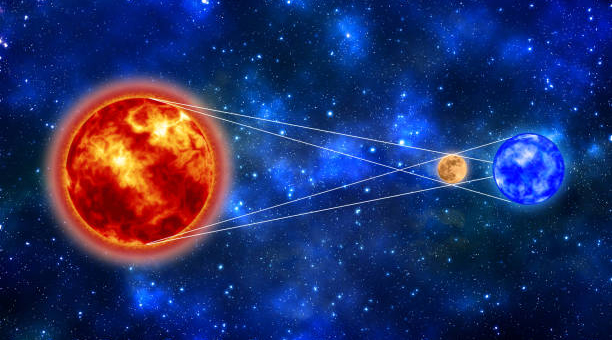理发吉日神定是什么意思(北京—纽约)

1988年10月底顾城与严力于纽约(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16日《南方周末》)
“北京—纽约”追记
严力 诗人、画家,现居上海
美国诗人金斯堡在1988年10月组织了一次名为“北京—纽约”*诗人在美国的活动,1987年底就落实邀请,以便*那边的诗人有时间申请护照和签证。
舒婷后来在一篇回忆顾城的文章中记录了这个活动的形成:
“1986年5月,我应邀去美国,先到旧金山,到纽约,再到明尼阿波利斯,到斯坦福、伯克利等好几个大学去朗诵和讲座。省里给的出国批文是三个月。在纽约时,与美国诗人金斯堡几次见面,他主持我的朗诵会,并邀请我到他家去喝下午茶。我们讨论商谈举办一场‘北京—纽约’的诗歌活动。*诗人名单由我提供。……那次活动究竟都有哪些诗人获得通行,我也记不得了。……*诗歌刚刚走出国界,朦胧诗大盛。一个个诗歌节、国际笔会、大学演讲、驻校作家的邀请纷沓而来。他们在世界各地漂泊,在上一个活动和下一个活动之中,去熟人、朋友家中过渡等待,甚至被安排或介绍到素昧平生的屋子里借居。”
1988年我已经在纽约第三年了,来参加“北京—纽约”活动的诗人几乎都是我之前在国内的朋友。10月底在纽约相聚时,很多纽约的文人艺术家在一家熟人开设的餐厅包下二楼办了一次聚会。我记得当时已在纽约的朋友有:作家曹又方,美洲华侨日报副刊主编王渝,作家丛甦、叶坦,*诗人、艺术家秦松,诗人李斐、张郎郎、沈忱等等。从*来的有北岛和邵飞夫妇、江河、公刘等。顾城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木耳(顾城夫妇去世后,朋友们捐款为桑木耳成立了“木耳基金会”,木耳之后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费用都是从这个基金会里获得的。)是从新西兰过来的,他们早在1987底就在香港获得访问新西兰的签证。顾城说,面签时,谢烨怀胎都快八个月了。她穿着宽大的衣服,怕露馅影响签证,结果顺利获得了签证。到了新西兰不久,他们也收到了“北京—纽约”诗会的邀请。
顾城的地址是诗人张真的先生马思中给我的,于是我与顾城有通信往来,他在1988年6月左右给我的一封来信是这样的:“严力不老兄,近安。《一行》收到,中有数友,幸得一会。我已收到纽约诗会邀请,故会之有期。夫人已有娃娃名木耳,忙之加倍。寸言不恭,顺附小诗。我的通讯处就是大学,马思中给的地址极对。臂长千里,隔海一握。顾城”
那伙人仍在载浪起伏吧
王渝 作家,现居纽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台北,我刚开始写现代诗就认识了秦松。还在上大学的王泉生和我竟跟一伙当大头兵的商禽、楚戈、辛郁、张拓芜等成为莫逆之交。大头兵是*对级别最低小兵的称呼。我们肚子饿了就去秦松那里,他会买一大堆肉包子来给我们吃。记得我出国留学前他们跟我喝酒,秦松频频叹气举杯对我说:“我同情你。”他的意思是我独自离开以后会很寂寞了。后来他也来了纽约,因为一张抽象画,被一位相当有名气的画家指称为倒写的“蒋”字。他在这里生活一直窘迫,终于画作有了市场,名利双收。可是,才过了两三年宽松好日子,天不假年,突然病逝。
初识顾城于北京,人与诗一般清纯。他那双寻找光明的黑眼睛,是一首绵延读不尽的长诗。后来,我再也不敢去想那双眼睛了。那次他来一直戴着牛仔裤管做的高帽子,那是他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据他自己说戴上高帽子让他有安全感,可以把他和别人分离开来。
1980年代*文学艺术上一片蓬勃生机,和国际的交流频繁。因为诗的缘故,除了顾城是远来的客人,其他几位都经常聚在一起。沈忱是画家,常给严力主编的诗刊《一行》画插图,构思新颖,笔触灵动,备受赞扬。张郎郎是多面手,也曾为《一行》画插图。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有次在文学讨论会上,即席成诗朗诵,充分表现了当时情景,获得满场掌声。虽然北岛习惯沉默,他永远是注意的聚光点。有时简直太过分。一次隆重的诗朗诵完毕,主办人在场外设置桌椅,让几位朗诵者为买了诗集的听众签名,结果只见一条长龙排在北岛的桌子前。从年轻时就开始写诗的李斐,其实很爱说笑,只是有口难言。他说普通话,我们宁愿他说广东话。他说广东话,我们又会叫他还是说普通话吧。诗人黄河浪却从他的诗读到一份无奈,说那是因为“唐人街是一种乡愁”。李斐写了不少关于唐人街的诗。严力和我的交往最为频繁,因为我编的副刊,也因为他创办的诗刊《一行》。他来到纽约,带动了诗坛,凝聚了诗友。他的人脉好,举办活动,总有人送来大批青岛啤酒,任我们喝个够。
年轻的诗友曹莉刚刚碰到过李斐,她说:“你们那时每个人都那么年轻那么帅!”接着,她传来写下的两首诗,在《那时的你们》中有这样的句子:也许没想到/请他们归还/从你那里夺走/最后的贴身之物/正被他们高价拍卖。曹莉在另外那首《对视》中问道:告诉我/大西洋久远的浪头/将你们拍到了何方/七零八落歇在了岸边/还是仍载浪起伏/享受弄潮。
有了曹莉这样的呼应,我想或许就是一种证明:那伙人仍在载浪起伏吧?

1988年6月顾城致严力信(资料图/图)
旅途,没有句号
沈忱 画家,现居纽约
这是1988年的深秋,为“纽约-北京”,老朋友们撞在了一块儿。“纽约-北京”的第一期是“北京-纽约”,一项由艺术家和诗人发起组织的活动,有艺术展览和诗歌朗诵会两部分。第一部分在北京和上海展出了22位美国艺术家的作品,第二部分落地纽约后怎么就升级为“纽约-北京姐妹城市文化交流”了。纽约画家Stephen Lane和Susan D’Angelo主持,我参与并协助。卡特总统和爱德华*来了贺信,中英文报刊杂志争相报道,好一番热闹。我们选择了15位*艺术家在斯坦顿岛海湾文化中心举办作品首展,伴随开幕式的是一场12位*诗人的诗歌朗诵会。其间另一场由艾伦·金斯堡和北岛领衔的诗歌朗诵会在MOMA举行。
我见北岛次数不多。从挪威穿上的厚毛衣都来不及换,大块的色域图案还带有北欧式的理性,不修边幅的长发和小胡子,日久发黄了的眼镜,给人感觉他仍然在旅途上。这样子也让我想起第一次见面,他的生日晚会,在北京阜成门外一座四合院。“海底的石钟敲响/敲响 ,掀起了波浪”,有人朗诵北岛的诗,东北口音深沉有力。三年前我去香港住他的书房,看到了他的水墨画,无线条无色块,满满一纸小小的点儿米粒般匀整,比我的作品更抽象更理性。我有点老花看着晕晕的,想像他的诗歌散文,一行行抽去了文字,剩下满纸逗号。听说他画点点儿有助于养神,神定了可以写长的。
头上永远套着那顶诗歌款式的裤腿笠帽,不用认就知道是顾城。在北京时从没见过他这副装扮,后来在照片上看到了他的笠帽,也许从那时候起,他老让我幻见太平洋某个岛族的神秘长老。这次他朗诵了只有两句的短诗《一代人》:“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以前我和顾城在一位瑞典朋友家里常见面,很多次一起吃晚餐,他都会带一些小玩意儿送给主人。他微眯眼睛羞羞地笑着,像讲解诗歌一样讲解他手中宝物沉淀的历史,如何护身的法力。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心里后悔自己没能写诗。不久就听说他去了新西兰,隐居在太平洋岸边的一个叫激流岛的地方,为了寻找他的光明。
我还真不知道郎郎从哪儿一夜间冒了出来,素未相识却成了我的Roommate。郎郎会写能画又很幽默履历丰富,我们一起去过格林威治村参加一年一度的鬼节Halloween*。郎郎装作骑士我扮成屠夫,挤进了缓缓行进的队伍。千姿百态的妖魔鬼怪潮起潮落,广场和街道水泄不通。我们心里既有点触动又莫名地兴奋。半夜深更冷飕飕地回到住处赶紧躲进被窝,迷迷糊糊在睡梦中我被一波波铿锵的颤音刺醒,我警觉那不定是什么真的鬼魂跟了进来。我起身哆哆嗦嗦循着颤音摸到了郎郎的床边,我真有点害怕了,这声音来自郎郎的身体!第二天他告诉我,那是他心脏金属启动片发出的声音。1980年代末刚来纽约的,脚根还未落地得先去见严力。那年头他正春风得意和日本女友住在东村十一街,在哥们儿心中有点“寨主”的意思。他当时正*持着《一行》,一行行串起了不少写诗的画画的当医生的做老板的大陆香港*的,当然,多数是从世界各地辗转进寨的北京老友,他家里一波接一波像过年似的,酒水不断。还真有几位医生老板喝啊喝,喝出诗句来了,一行队伍日渐壮大。当时我们在街上画肖像生意不好,就去八街那些破烂旧货地摊觅宝,两手空空蹿到严力府上喝几口烈的驱驱霉味儿,为明天交个好运。我白天在Studio School上学,课堂上偷偷为《一行》画些插图,跑亚美协会冲着朋友们义卖,为杂志募捐。有几次还卖得不错,就杀到十一街给严力满上几杯。严力酒量好,写诗前还必须喝到位。
在纽约华人文化圈里王渝算得上是沙场老将,却少有当家人的架势。她善良几近单纯,健忘也那么幽默,我们是鸡犬之声相闻老*不相往来的老朋友。她的儿子刚上大学,请她寄了几本书。儿子收到邮件,从里面取出来的,是两包已经发霉的麦当劳汉堡包。那年我和夫人在巴黎去毕加索博物馆,排队拐弯刚要踏进大门,突然被熟悉而又久违的呼声绊住了,扭头一看,颠颠匆匆的王渝急步向我们走来,笑眯眯的,红光满面,酒气袭人。我愣了一下,说王渝你真行大白天喝得醉醺醺的跑这儿干嘛来啦。“我来看毕加索啊,之前无意喝了点儿剩酒。”我进得馆里望着《斗牛士》,琢磨来琢磨去,这才觉得王渝厉害啊,要不喝点儿,还真不容易看毕加索。
本文链接:http://xingzuo.aitcweb.com/997414.html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